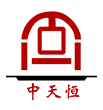资讯详情
检方首次公开回应李蕊蕊案审判结果
如果不出意外,1月14日,安徽籍上访女子李蕊蕊将在其舅舅王忠诚的陪同下再次抵京,为案件的抗诉奔波。
此前,李蕊蕊曾欲向检方递交《抗诉申请书》,然而,在李蕊蕊递交抗诉申请书之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已对此案刑事部分提起抗诉。 检方抗诉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其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检方在抗诉书中称,被告人徐建系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检察院以其触犯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3项之规定提起公诉,认定徐建属于强奸罪的情节加重,应当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进行判罚。而一审判决对于徐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事实予以了确认,但引用了刑法236条第1款进行判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3项规定,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根据刑法236条第1款,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二,徐建的自首情节并不能使其获得减轻处罚。检方在抗诉书中称,徐建利用其看管上访人员的身份,在多人居住的房间内强奸李蕊蕊,而李蕊蕊系边缘智力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发案时性防卫能力减低;并且这一强奸行为被当时在屋内居住的多人所感知。后徐建锁门离去,屋内多人破门而出,与李蕊蕊共同报案后又接受了媒体采访。此案一度引起过社会关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一过程,足以反映出徐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对被害人的伤害程度。
检方称,公诉机关虽然对于徐建的自首情节予以认定,但不建议法庭对其减轻或者从轻处罚。一审判决对徐建予以了减轻处罚,因而在10年有期徒刑以下进行量刑。检方认为,一审判决对于自首条款的运用脱离了全案的基本事实和情节,适用不当,因而对于徐建的判罚属于量刑畸轻。
检方的抗诉能否得到法院的认可,尚未可知。针对此案的抗诉依据及社会意义,《法治周末》记者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法学博士刘涛进行了解读。
刘涛认为,丰台检方的抗诉无疑是正确的,其深意在于对刑法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契合一致的追求。
刘涛分析,丰台法院适用刑法236条第1款进行判罚存在着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之间明显的冲突。
虽然同是强奸罪行,但是由于行为目的、行为方式、行为后果的不同,刑法规定了不同的处罚等级。故我国刑法236条在第二款和第三款针对较为恶劣的强奸行为规定了较第一款更为严厉的处罚。
丰台法院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被告人徐建的行为系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则必然适用相对应的第三款,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法律适用最基本的逻辑对应性,满足刑法规范对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内在符合。
针对检方的第二点抗诉理由,认定自首但不建议减刑,刘涛解释,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从中可以看出,刑法在关于自首的适用过程中,并没有将自首与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结果之间赋予必然的联系,而是将这个联系的取舍交给了司法的自由裁量权来解决。
法律规定自首,其价值取向就是在惩罚犯罪的基础上,通过自首制度的实施来获取公正对待犯罪人,同时有利于国家、社会的预防犯罪的结果。要达到这种结果,则必然通过对作为犯罪行为可罚性本质的社会危害性的考量。
从本质上而言,对于一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考量,要充分评估预防行为发生的成本与行为潜在影响人群的寡众。如果一个行为对于行为人而言预防成本很小,而行为人宁愿舍弃这种成本追求犯罪的获利,则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同时,如果一个行为潜在影响人群较多,则社会危害性较大。
徐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较大。本案中,徐建的身份独特,作为看管上访的人员,其代表并实现着国家对社会管理的职能。这种职能的本质乃是为社会服务,而非恣意的侵犯社会秩序。
而该职能的滥用,对于社会公众心理而言,不仅仅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权威性,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安全感和信任度。因此,徐建行为社会危害性之深,已经不足以通过自首的认定而从轻或减轻处罚。